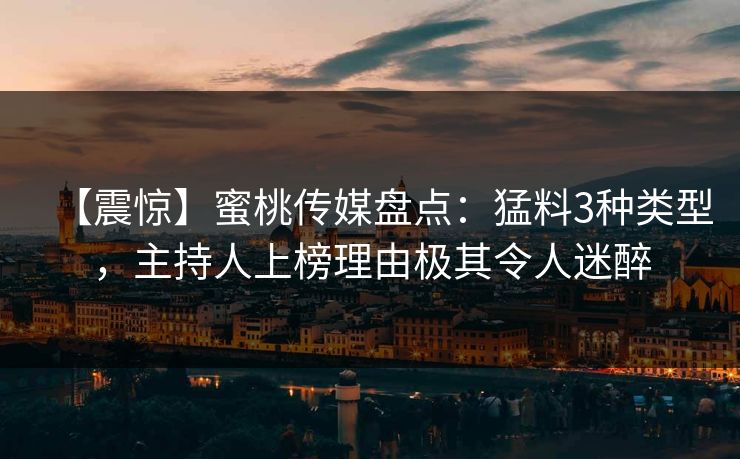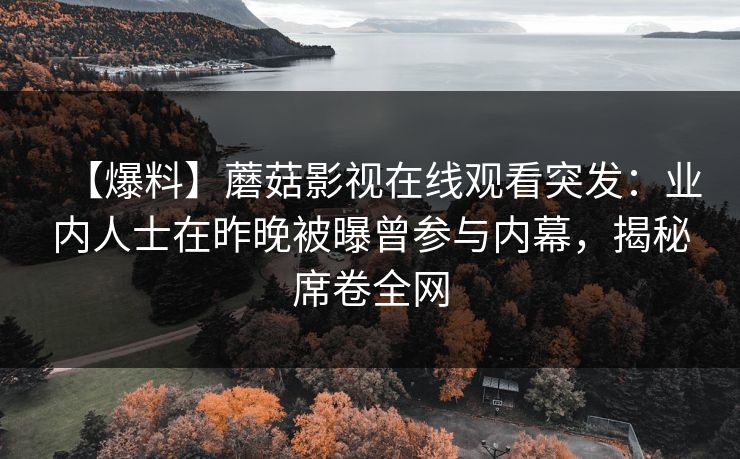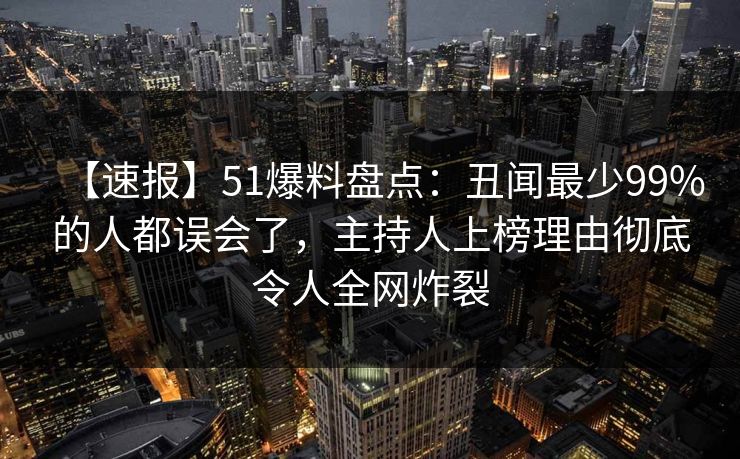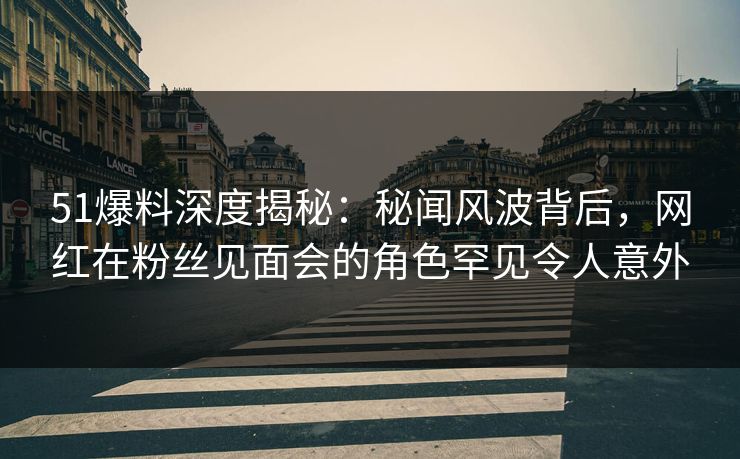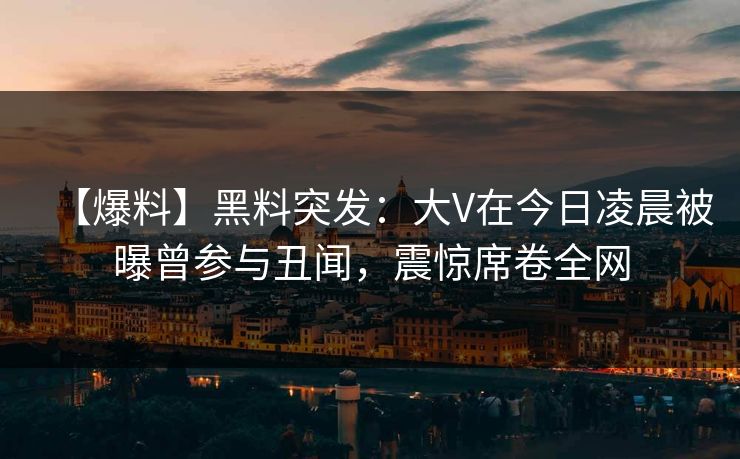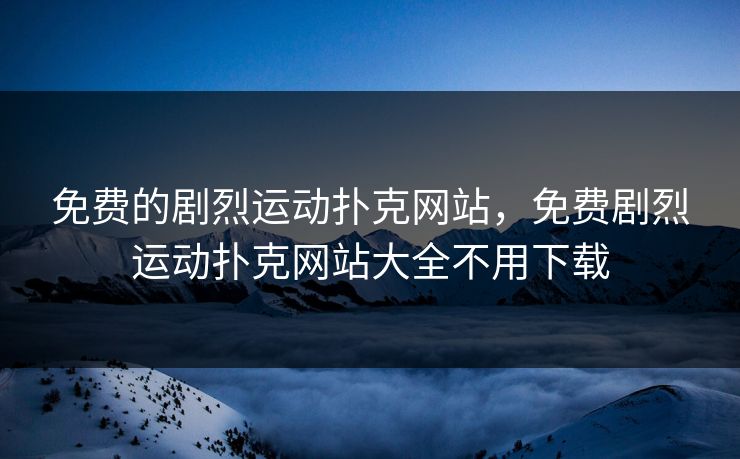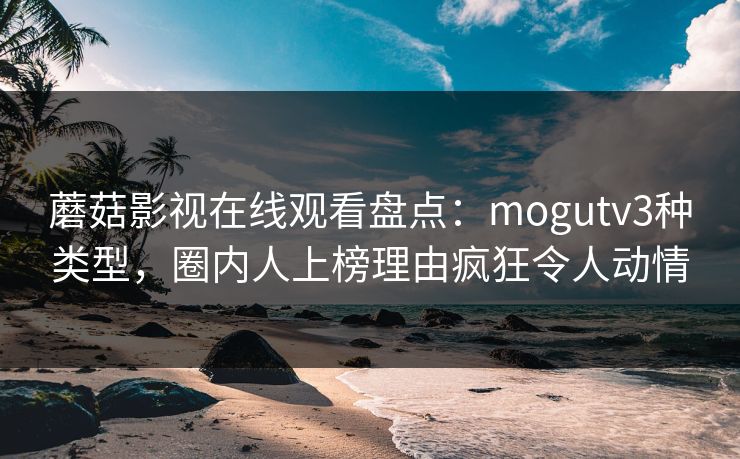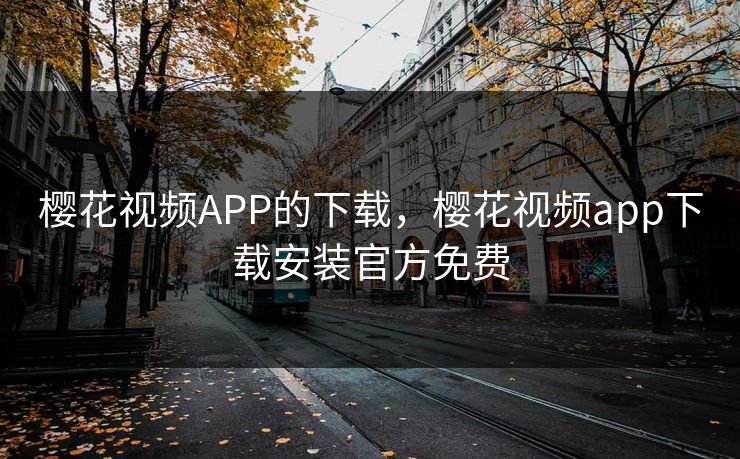扎根现实,映照灵魂:陈雪与她的“老牛耕田”文学世界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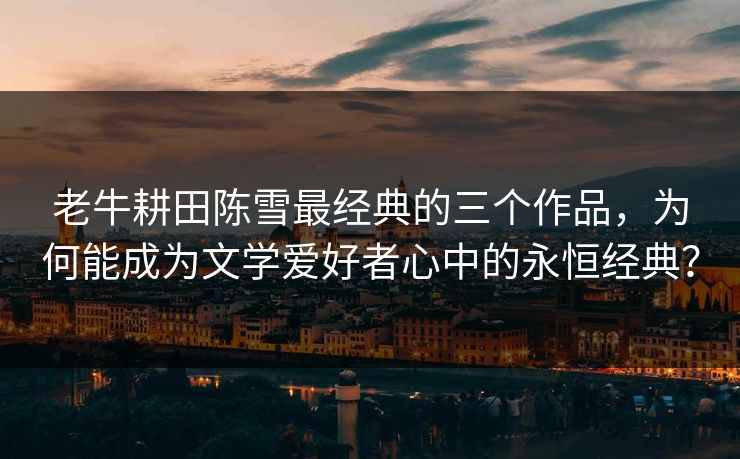
如果把文学比作一片广袤的土地,那么陈雪无疑是那位执着耕耘的“老牛”。她以文字为犁,以生命经验为种子,开垦出一方充满韧性、挣扎与救赎的文学风景。而她的三部经典作品——《桥上的孩子》、《附魔者》与《无人知晓的我》,恰如老牛耕田中翻出的三块沃土,层层叠叠,既沉重又丰饶,既痛苦又充满希望。
《桥上的孩子》作为陈雪半自传体小说的代表,可以说是她文学宇宙的奠基之作。这部作品以极其坦诚的笔触,回溯了一个在贫困、家庭暴力与性别困境中挣扎成长的女性生命史。书中的“桥”不仅是地理空间的象征,更是主人公介于童年与成年、绝望与希望、创伤与愈合之间的心理临界点。
陈雪不避讳描写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匮乏,却从未让叙述沉溺于哀怜。相反,她以近乎冷冽的诚实,呈现出一种“老牛耕田”般的耐力——即使背负重轭,依然一步步向前。这种文字的韧性,让读者在压抑中看见力量,在破碎中感知完整。
值得一提的是,陈雪在叙事中大量使用具象的日常细节:一碗勉强果腹的稀饭、一件反复缝补的校服、一场无声的母女对峙……这些细微之处并非只是为了渲染苦难,而是她扎根现实、映照灵魂的方式。正如老牛耕田,一犁一锄看似平凡,却翻开了土壤之下的真相。正是这种对生活本相的忠诚,使《桥上的孩子》超越了“悲惨故事”的框架,成为一代人精神困境的文学备忘录。
而《附魔者》则进一步展现了陈雪在处理人性复杂面上的卓越能力。这部小说以多重叙事视角,探讨了爱情、欲望、罪疚与自我欺骗之间的模糊地带。书中人物如被“附魔”,在激情与理智的拉锯中不断坠落与攀升。陈雪以其特有的心理洞察力,细腻剖白了人在情感困境中的执迷与觉醒。
她并未给出简单的道德评判,而是如同一位冷静的耕作者,耐心地挖掘人性深处的光明与阴暗。
“附魔”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耕田——耕的是心灵的荒芜与混沌。陈雪通过角色的内心独白与对话,呈现了情感如何既能滋养人,也能摧毁人。这种处理的深刻性,使得《附魔者》不仅是一部情感小说,更是一份关于现代人精神存在的研究报告。读者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他人的故事,更是自己的影子。
从伤痕中开出花来:陈雪文学的治愈与超越
如果说《桥上的孩子》和《附魔者》更多聚焦于个体的创伤与挣扎,那么《无人知晓的我》则将视角转向了自我和解与身份重构。这部作品延续了陈雪一贯的坦诚与锐利,但多了一层温润的治愈色彩。书中通过日记体、书信与碎片化叙事,拼贴出一个试图在迷茫中寻找“我是谁”的现代人画像。
这里的“无人知晓”,并非指向孤独,而是指向一种唯有自身才能完成的救赎。
陈雪在这部作品中展现了惊人的文学控制力——她让痛苦发声,却不放纵悲伤;她允许困惑存在,却不放弃追问。正如老牛耕田,不以速度取胜,而以深耕为志。她笔下的人物在反复的自我质疑中,逐渐学会接纳残缺、拥抱真实。这种从“无人知晓”到“终于明白”的过程,恰恰是文学所能提供的最深刻的慰藉之一。
读者跟随叙述的脚步,仿佛也经历了一场内心的犁垦,旧伤被翻开,新芽却在黑暗中悄然生长。
陈雪的作品之所以被广泛认可为经典,不仅仅因为其文学技巧的成熟,更因为她始终坚持以“老牛耕田”般的耐心与坚持,关注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边缘经验。她写家庭暴力下的童年,写酷儿情感的纠葛,写经济窘迫中的尊严挣扎——这些题材本身极易被简化为猎奇或煽情,但陈雪总能用沉静而有力的文字,赋予它们普世意义上的共鸣。
她让读者意识到,那些看似私人的痛苦,其实连接着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与人性共通命题。
陈雪的叙事往往带有一种“正在进行”的即时感。她很少以全知视角总结人生,而是让角色活在困惑里、长在挫折中。这种未完成性,恰恰是对生命本质的忠实摹写。人生不是一场结局既定的戏剧,而是一片需要不断耕耘的土地。而陈雪就像那位永不停歇的耕牛,以文字为媒介,一遍遍提醒我们:痛苦不必回避,伤痕可以开花。
从《桥上的孩子》到《附魔者》,再到《无人知晓的我》,陈雪用三部经典作品完成了她对人性、创伤与救赎的深度探索。她不高喊口号,不贩卖希望,却以一种近乎固执的诚实,犁开了现代人心灵的荒芜之地。或许这就是“老牛耕田”的真正含义——文学不必华丽,但要深刻;不必轻松,但要真诚。